杏彩体育地址-太阳队战绩起伏不定,寻找稳定表现
莫言与刘庆邦及其他
作者:王安忆 原载:《青年报》2017年9月10日第A5版
王安忆肖像 陈婉清绘
莫言有一种能力,就是非常有效地将现实生活转化为非现实生活,没有比他小说里的现实生活更不现实了。仿佛他看世界的眼睛有一种屈光功能,景物一旦进入视野,顿时就改了面目。并不是说与原来完全不一样,甚至很一样,可就是成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世界里的一切还是依原来的样式链接镶嵌,色彩却全变了,很容易将其视作为一种风格,但风格其实是装饰的意味,这里的色彩则影响到事情的性质。这“色彩”更接近“质地”的意思,事情的质地不同了,于是,就变得不那么真实。在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,比真实的更为沉重,但确有着一重意境。小说实在是一种过于结实的东西,现实既是它的内核,又是外相,要从中抽离出一个独立的世界,是需要更有力量的占位。
我想用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说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——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可能性。故事讲的是三十年前的大羊栏村,离村庄三里地处,坐落着一个胶河农场,聚集有四百多名右派。莫言这么写:“从很早到现在,‘右派’在我们那儿,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。”对这些身怀绝技的能人,村人们有着极高的褒奖,就是“不善”。这句评语很奇妙,从字面上看,是可视作一个颠覆,透露出这个故事是在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语境中发生。
我描绘了莫言小说世界的轮廓,再用几项对比来进一步分析这世界的性质。第一项对比,在莫言与刘庆邦之间进行。
刘庆邦是儒家,承认现实秩序,遵从它,担负起伦理中的责任。他有个短篇小说,写一家农户,父亲去世,余下孤儿寡母,长子还在幼年。生产队里分粮食,倘若是红薯,一家一堆,最大的红薯上就写着一家之主的名字。母亲就让会计写上长子的名字,从此,这个小男孩就承担起家庭的重任。刘庆邦笔下的人和事,就是被规定在伦理的秩序内,承上启下。代和代之间呈现和谐宁静的关系,这种关系经过数百数千年实践检验,合乎生存的情理,结构稳定平衡,亘古不移,无论改朝换代,纲常变迁。礼失而求诸野,这个“野”,就是刘庆邦的小说世界。在那里,能看见某种程度和形态的礼仪,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,被赋予了美学的意义。

他有一篇小说叫《种在坟上的倭瓜》,描述了这日常化的仪式里的抒情性。小姑娘猜小,带了弟弟给刚去世的父亲上坟。觉得父亲身后薄瘠凄凉,思忖着在坟上种点什么,最后决定种一棵倭瓜。讨来一粒籽,小心翼翼埋在坟脚,接下去就是无限担心:担心老鸹偷吃了倭瓜籽,担心种子不发芽,担心日头晒狠了,担心雨水泡烂了;终于出芽长叶,这担心就加剧了,担心腻虫啃了,担心割麦人错割了,还担心淘气的男孩摘了瓜纽子……千担心万担心,坟头覆上绿油油的藤蔓叶子,结出一个金红色的大倭瓜。姐弟俩去收获,坟上的繁荣景象将伤心洗涤而尽,高高兴兴抱了瓜回家了。刘庆邦的书写往往是伦常里的诗意,承继和成长怀着虔诚的驯顺。比如又一个短篇小说《鞋》,说的是一个名叫守明的闺女,给订了亲的未婚夫做鞋。乡间的规矩,男方下过聘礼,女方就要回礼,回什么呢?做一双鞋。闺阁中第一次接触异性的物件,是托付自己一生的那个异性,做这双鞋有多么隆重,又有多么害羞。千针万线,还不能让人看见嘲笑她,就得躲着,其实躲的是闺女的心事。刘庆邦世界里的成长从现实的传统里出发——在无论时世如何变化也不改初衷的那一个永恒的循环里,担着自己应尽的义务,忠实诚挚地施行人生的使命。在他写农村生活的同时,还另有一个分量相等的写作,就是煤矿上的社会。在那里,刘庆邦是要激烈许多,因为面对一个和谐秩序的崩溃,是构成他的世界的相对面。
莫言世界里的成长,是在抵抗中进行,这抵抗称得上酷烈。短篇小说《拇指铐》可视为对这成长的隐喻。小孩子阿义,为生病的母亲去抓药。阿义黎明时动身,路遇的人如同鬼魅幽灵,无论阿义如何述说母亲病情的急重、抓药的殷切,都像是朝着虚空茫然。终于抓到了药,转身向回家的路上奔跑,无意中却闯入一对男女奇怪的幽会,于是被逮住,囚禁在树上。铐住他一对拇指,可十指连心,连动弹都动弹不得。有一些人从身边走过,却都冷漠地离开,抛下他一个人,历经炎日、大风、冰雹,四面是起伏的广漠的麦田,还有古怪的野唱,这一切就像是铜墙铁壁,阻断了与外界的互往沟通。他以非常残酷的自伤脱离拇指铐,落回到地面上,最后一段是这么起句的:“后来,他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赭红色的孩子,从自己的身体里钻出来,就像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一样。”我把这情景当作象征,象征莫言世界里的成长方式,就是像蝉蜕一样,自己从自己里面脱出来,脱出来,然后成熟,长大。
莫言的成长往往是一个激动的过程,母亲的愤怒,父亲的浪荡,创伤,疾病,谩骂,暴力,遗弃,可是孩子并没有因此萎缩;相反,很健壮。《麻风的儿子》里的儿子,也是《姑妈的宝刀》里麻风女人的儿子,张大力,非但不得这可怕的遗传;相反,皮肤光滑,力大无穷。《弃婴》里那个生在葵花地里的女婴,也是健康漂亮,食量极大,生长迅速……莫言世界里的生命,仿佛金石迸裂,石破天惊,将个好端端的天地又推进蛮荒,这蛮荒不是那蛮荒,那蛮荒是文明之前,这蛮荒却是文明之后,所有的人工全又断成碎片,重新化成混沌。
刘庆邦的世界是人力可为,一针针地走线,一粒粒地下种,庄稼一季季长和收,人一代代地送走又迎来。莫言的世界是被不可知的力量所控制。短篇小说《大风》,故事很简单,爷爷与孙子一同去草甸子割草。祖孙俩早早起身,沿着河堤往草甸子走去。祖孙俩都不说话,天地间似乎有一股肃穆,晨雾渐渐退去,东方发红,“太阳一下子弹出来”。莫言将这场面写得十分壮观,他的语言有一种绚烂,不是说他用了什么华丽的字和词;相反,都是大白话,是最直接的叙述,比如“像拉了一下开关似的,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,照亮了天,照亮了地”。都是简单的动词和比喻:“拉一下开关”,“射出来”,“照亮”,然后是:“河面上躺着一根金色的光柱,一个拉长了的太阳。”四下里还是寂静一片,爷爷却哼起歌来,这早起行路的旷野就散发出恒古的意境,地老天荒。到了草甸子,割草、扎捆、装车、上归途,可是天色变了,大块乌云疾速漫过来。爷爷脸色变得严峻,“木木的”,可有一瞬,孙子却看见爷爷“眼泪汪汪”,分明已经领了天地间的预兆。风起的那一刻,是一个无限的寂静,庄稼叶子、河水,都在动;野蒿子、野菊花全在喷吐芬芳,可就是没有声音。蚂蚱、野兔,都在跳跃,还是没有声音。然后,风来了。这是大自然无可抵御的力量,要制伏它根本没有可能,爷爷是识时务者,以静待动,等待大风——天地间一次暴躁的任性发作结束,终于,一切平息下来。莫言写道“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”,大自然既是蛮横无理,又有着极美的姿态,真是不可知啊!车上的爷爷割了一日的草,全被风卷走了,只在车梁的榫缝里留了一棵,是从大风的罅隙里漏网的一株生命。

刘庆邦的世界是人与自然讲和的,不是说自然怎么善待人,而是人因循着规律办事,所以,刘庆邦的世界是人道的世界,而莫言就有些神道了。在刘庆邦这里,人都是常情的人,按着常理出牌,也由常情常理演绎成可歌可泣。但切莫以为刘庆邦的世界严谨缜密,就缺乏了风趣,其实不然,也有一股子俏皮劲:比如有一个瞎子,偏偏名字却叫“瞧”,人也是风流的;比如《嫂子与处子》,二嫂专喜欢逗民儿,民儿还是童男子,到底抵不过有经验的媳妇的攻略。二嫂做闺女的时候不敢怎么的,做了媳妇就不同了,可以放肆,就是说,“她对每个男子都要研究研究”,仿佛女性意识觉醒了。而且,像二嫂这样解放的女性不止她一个,还有一个会嫂,也喜欢民儿。这地方规矩是规矩,可好比关一扇门,就会开一扇窗,叔嫂间无论闹得怎样山重水复,都不兴着恼的,在严格的伦理中,自有一番热闹。
莫言笔下的人和事都是超乎凡俗的。乡间是火辣辣的世界,太阳特别耀眼,老蒺藜的刺格外坚硬尖利,夜晚黑得迸火星,雷雨天遍地滚着球形闪电,黄麻、芦苇、大草甸子密得打墙,成熟的麦田亮得晃眼。广漠的悲哀,是莫言辉煌世界的底色。莫言的世界虽然如此离奇,但决不是臆造的,是将人世折射成另外一个形式。外乡人进城谋生计,在他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中的情景是,“一个乡下人骑着像生铁疙瘩一样的载重自行车,拖着烤地瓜的汽油桶,热气腾腾地横穿马路,连豪华轿车也不得不给他让道”——多么有豪气,一巴掌将城市从文明中打入草莽。
将莫言与刘庆邦对比,其实是尝试与一个写实的书写相比照,以严格正统的世界反射出另一个背离的世界。
再要进行一项比照,就是作家们各自笔下的孩子。孩子是每个作家免不了要写的,在有些作家,只是作为写作对象的一部分;在另一些作家,孩子却意味着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。比如苏童的小说,有许多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讲述,这个担负讲述任务的小孩,其实是带着世人的眼睛,是世人中间最清澄,最公正的眼睛。
第三项对比,是在莫言小说世界的内部进行。莫言的世界,由两块地方组成,一块地方是极其的聒噪,另一块地方,则是静默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的黑孩,都以为是个小哑巴,无论多么疼痛、不公平,都不叫唤;欢喜时也不叫唤,大约因为无人能与他分享吧!而在这一块静默的周围,却是吵得人耳朵疼,都是会说话的人。《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》,写村人逮住一匹狼,拴住一条后腿挂在树上。整座村落都沸腾起来,先是大人孩子互相吆喝着去看狼,一片喧嚷;然后,逮狼的许宝开始讲述经过,众声止住,替换成许宝冗长的独白,虽然是独白,也是热闹的,声色动静,起伏跌宕;接着众声再起,因有个孩子就好比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那个诚实的孩子,指出那不是狼,而是狗,一场激烈的争论展开了。而自始至终,狼保持沉默,是万声喧哗中一个深刻而危险的静默。
莫言世界里的喧哗似乎是一个彻底的释放,将所有不可忍的一股脑儿叫喊出来,然而,好比此时无声胜有声,那叫喊响到极处,闹到至深,却是静默。大风来临,天地一片静谧,四下里的动物植物都在无声中被撼动。莫言还常常写到哑巴,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的黑孩不论真哑假哑,总归不出声;《白狗秋千架》里是一窝哑巴;《姑妈的宝刀》里的姑妈的三个女儿中,最漂亮的三兰就是个哑巴,最后却是她得了宝刀做陪嫁。哑巴似乎是个明喻,更多的是那一类沉默不语的人,《弃婴》里那个谁也不要的女婴;《金发婴儿》里被扼死的婴儿,他们都是没法说话的人。
当我将莫言与刘庆邦作对比的时候,说刘庆邦是儒家。莫言是什么呢?莫言的家乡高密,春秋时属齐国,齐国风气不忌讳怪力乱神,却是子不语,假如非要给莫言哲学的归纳,那么就定作道家吧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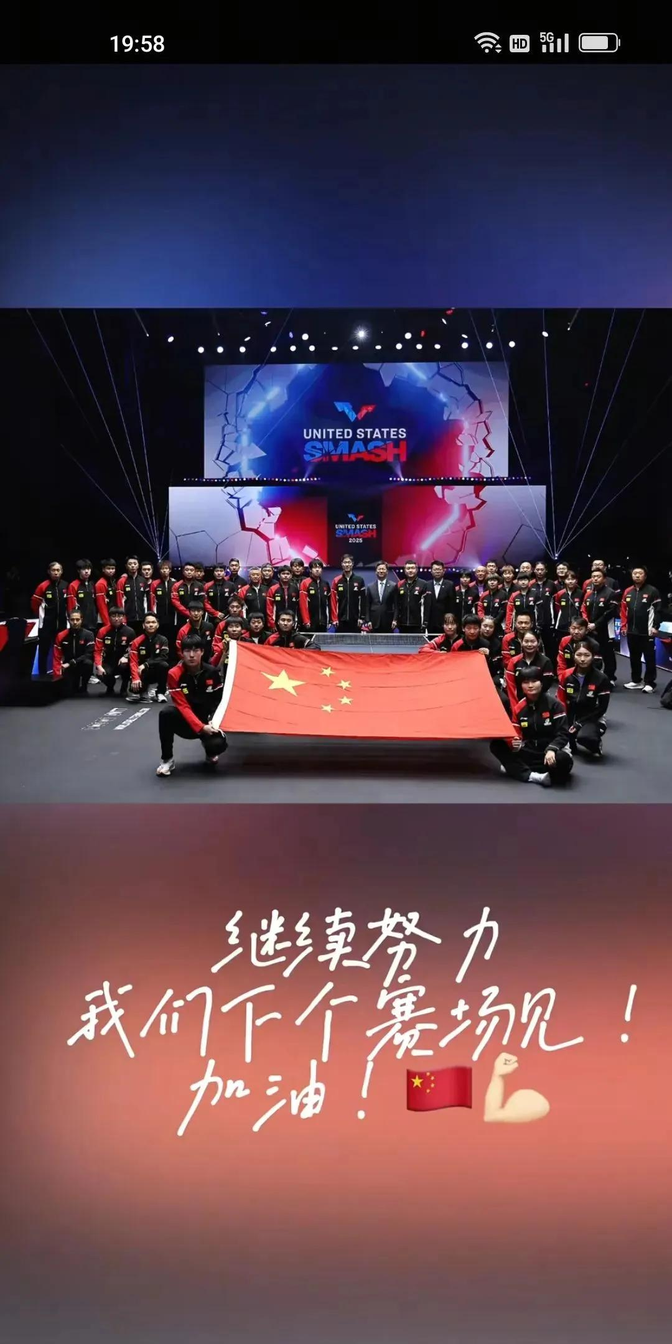

评论留言
暂时没有留言!